父亲和我与文化馆的不解之缘——邹平县韩店镇西王糖业公司 时佃书
题记:一本书,让我结缘文化馆;一座文化馆,情系两代人。父亲和我,与文化馆的故事,正在继续……
(一)
2015年,父亲外出串门时带回来一本杂志,轻轻地放在我的电脑桌上。他说这是县文化馆出版的一本杂志,文章不错,让我抽空读读,如果有兴趣,也可以投稿试试。当时,我正忙着在电脑上写东西,只瞥了一眼,也没当回事。毕竟,在这本杂志不远处,还摆放着几十本《读者》《意林》《散文》等知名杂志。
某日有闲,突然想起父亲给我的那本杂志,便找出来浏览一番。没承想,这本刊名为《邹平群文》的杂志竟成了我和文化馆相识的红娘。杂志名字很普通,封面设计很朴素,便对文字有无可读性产生质疑。带着这样的情绪,我随便翻开一页去读。不知不觉,竟被文字吸引了进去。一本小小杂志,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等体裁均有涉猎,可谓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”。或许是家乡人写家乡事自带的那种亲切感吧,书中无论写史描人,还是状物言情,都引起了我强烈的心灵共鸣。这些可读可亲的文字,使我对家乡故里的前世今生、风土人情有了更加透彻清晰的了解,也激起了我写作的欲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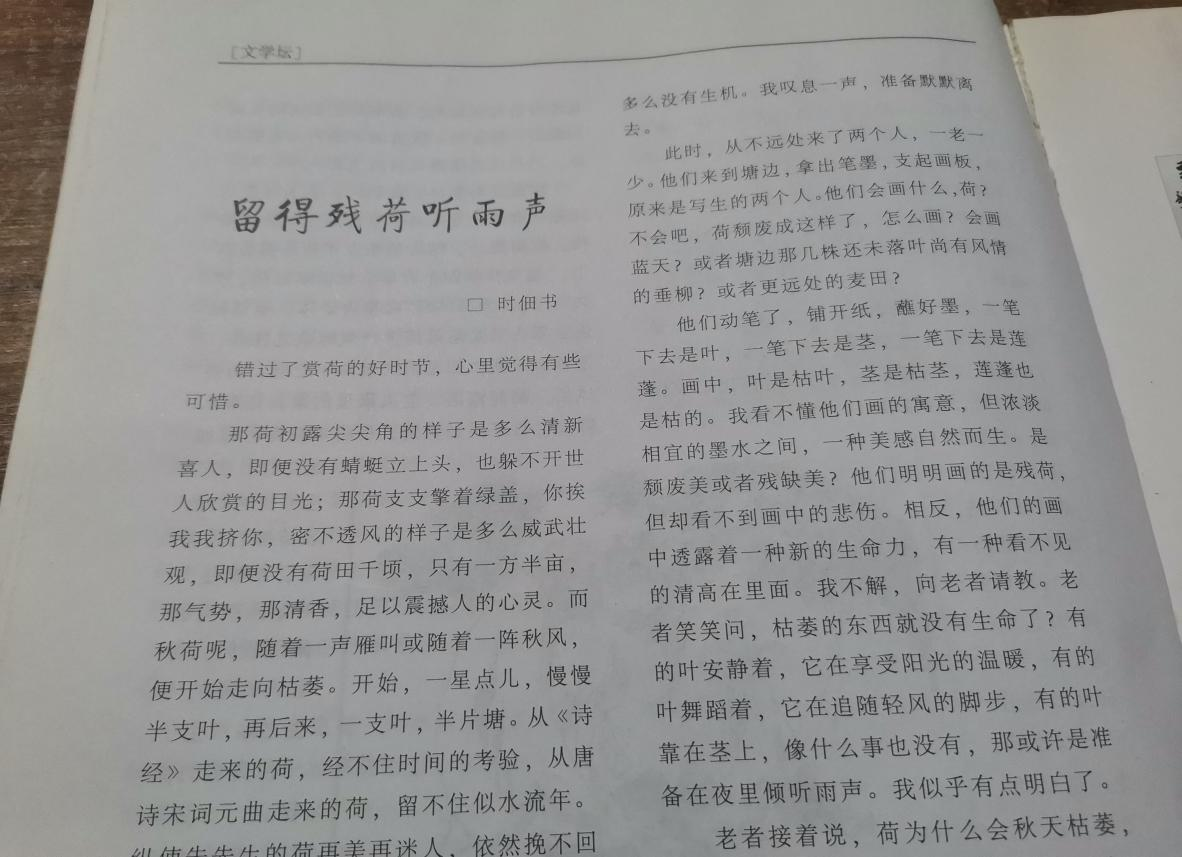
(发表在《邹平群文》上的第一篇稿件)
为了一炮打响,我从熟悉的事物入手,根据自身经历,精心构思,反复修改,创作了散文《留得残荷听雨声》。稿件投送之后,如石沉大海,杳无音信。心情由开始的忐忑不安、焦急盼望,慢慢变为淡淡烟云。当我头脑中已忘却此事时,却在投稿几个月后,意外接到稿件被2015年《邹平群文》第四期录用的通知。《留得残荷听雨声》发表后,受到县作协副主席范廷伟老师的肯定,在他和文化馆编辑老师的鼓励下,我创作热情高涨,相继又发表了《四月香椿来》《谷荻》《长寿花儿冬日开》等文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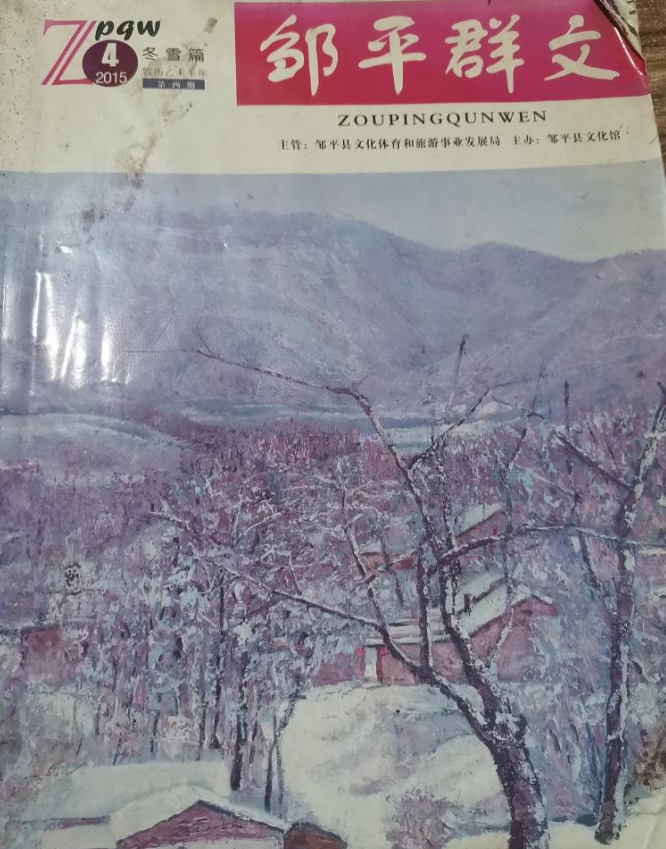
(《邹平群文》某期封面)
于是领取样刊,领取稿费,和编辑老师沟通文学创作,成了我与文化馆联系的常态。由此也认识了县内许多优秀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。文化馆平时免费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和培训,只要有机会我都积极参加。我不仅聆听过著名散文大家李登建先生的文学讲座,看过书法名家郭连贻、张延龙、王奎强等人的书法展,而且在文化馆领导的支持下,我和杨永、尚夏等老师还联合搞过水彩画展。当我的一幅幅水彩作品在文化馆大厅里展出时,自豪感、幸福感油然而生。谁能想到一个普通的老百姓,其业余爱好还能登入大雅之堂呢!每次想到这些,心里都是满满的感动,我知道是文化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放飞自我的平台,让我们尽情歌唱、尽情创作、尽情成长。
俗话说,“一枝独秀不是春,百花齐放春满园”。因受到文化馆恩泽,自己有了些许收获,带着一种独乐不如众乐的想法,我将《邹平群文》杂志推荐给公司爱好文学的同事们,并鼓励他们不怕失败,大胆投稿。在我的带动下,同事左丽宁、胡付营、王冬良等人迅速成长,成为《邹平群文》文学创作的骨干力量。在此基础上,部分同事再接再厉,多篇文章还发表在省级刊物和“学习强国”上面。这些成绩的取得,对我们文学爱好者来说,是多么大的激励和鼓舞啊!
因一本书,爱上文化馆;也因一本书,让我发现了父亲与文化馆鲜为人知的秘密。
(二)
《邹平群文》是父亲给我的最好礼物,它为我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另一扇窗。每当有新文章发表,我会把样刊第一时间送给他。七十多岁的人了,眼睛已经有些花。他坐在桌前,颤颤地打开眼镜盒,戴上镜子,从目录上一行行搜索我的名字。然后,左手大拇指沾下唾液,翻到我文章所在的页码,细细地读起来。他的神情很严肃,像在挑我文章的茬。我小心翼翼地站在一侧,静等父亲对我文章的评价。可他每次看完都默不作声,只继续看他人的文章。我知道,他已沉浸在文字的世界了。
素来少言的父亲,每每看完样刊,不由感叹几声,又只言片语地说起以前的点点滴滴。从父亲的喃喃自语中,我才惊奇地发现,半个世纪前父亲就和文化馆相熟。原先的老文化馆在什么地方,搬过几次家,他说得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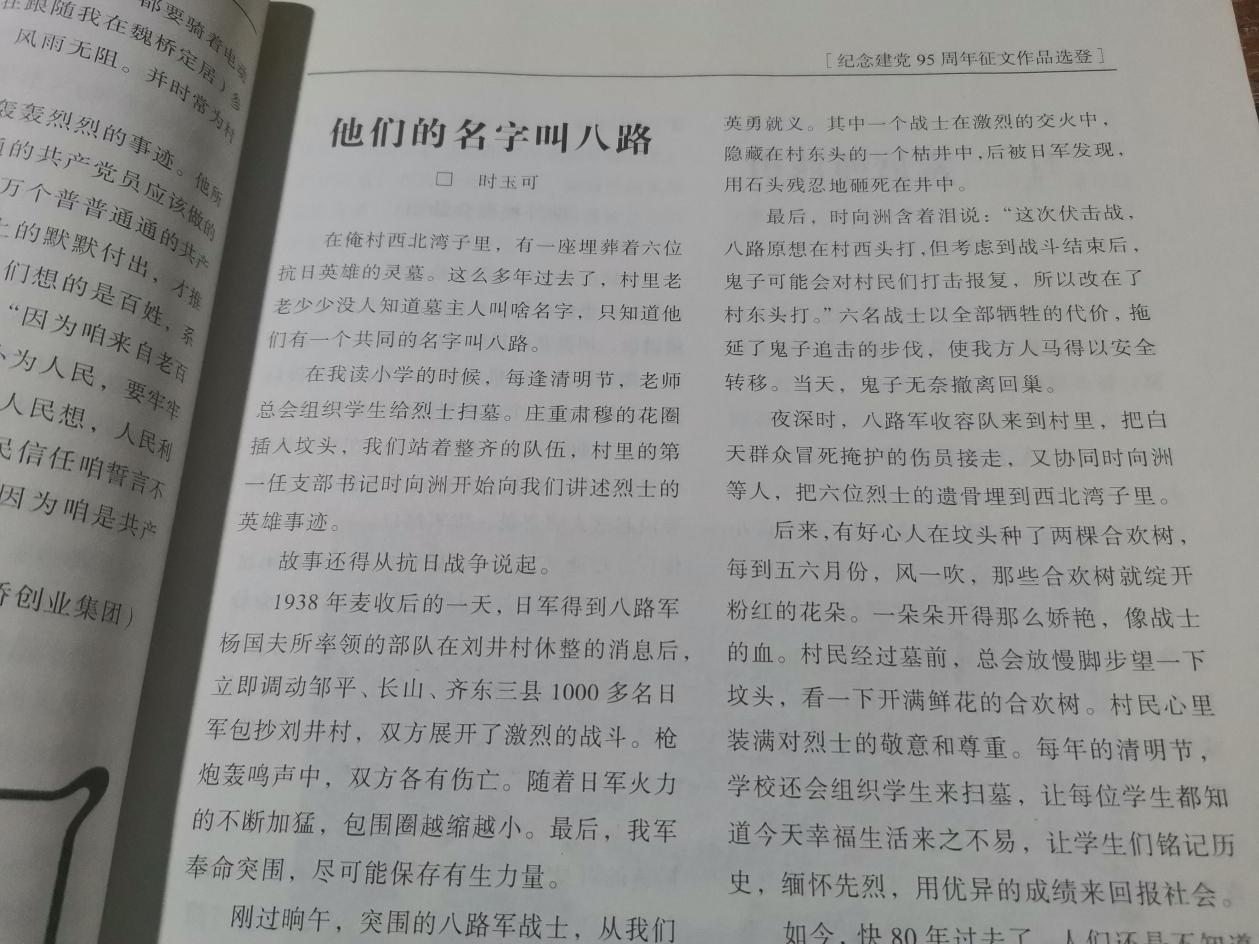
(图为父亲参与文化馆建党95周年征文获奖作品)
父亲说,那时文化馆没有什么杂志,只有街头文艺,在墙上张贴好人好事之类的报道。那时稿件全部是手写,专用的稿纸,镇上没有,父亲只能借辆自行车前往文化馆。来回五六十里的路程对现在来说,不值一提,但在半个世纪前,在道路坑坑洼洼、交通工具受限的情况下,骑车或步行,也是很耗费体力的。即便如此,父亲为了写稿件,每月也要往返县城三五次。去的次数多了,和文化馆的人员也熟悉了。至今父亲还记得高馆长,负责借书的孟凡静,录像的李老师,画画的张老师,至于馆员袁瑩、王红,因为他们负责审核稿件,父亲与他们更熟悉些。
作为一名农村通讯员,父亲是颇感自豪的,对写稿件也是充满激情的。在干完农活之后,他常常走村串巷,寻找写作素材,每个月都要投稿十来篇。那时投稿,除了去县城拿稿纸顺便将稿件直接交到编辑手中外,大多数稿件都要通过信封邮寄。说到邮寄,父亲眼里闪出一丝光。他用手比划出“八”,说,平时的信件都是贴八分钱的邮票,而我们通讯员只需要三分钱就行。这时,他的手势已经由“八”,变成了“OK”。知道吧,通讯员的信封还有特殊的标记,信封有四个角,要割掉其中一个角的角尖,然后在割角处写上“稿件”二字方可,不然,邮资就不是三分,而成了八分。
文化馆每年都会组织通讯员年会,让县内优秀的通讯员汇聚一堂,相互认识交流,共同学习进步。当时我们镇上,只有父亲一人有资格参加。有一年,因为通讯报道成绩突出,山东省广播电视台还给父亲发了个通讯员证,引来无数人羡慕的目光。说到这些,父亲眼里的光更亮了,脸上的皱纹也笑开了花。说实话,我很少看到父亲这样开心地笑。回忆起文化馆的点滴,一定有什么触动了父亲的内心深处。
上世纪70年代后,父亲因换了工作,加上结婚生子,生活的劳累渐渐消磨了父亲与文化馆的联系。这一断就是四五十年。但肯定的是,在与文化馆中断的几十年里,父亲一直留意着文化馆的变化发展,只不过他把这些关注、怀念,默默地、深深地藏在了心底。
刹那间,我好像突然明白了父亲给我《邹平群文》的原因。当他在朋友家无意看到文化馆出版的杂志时,内心一定是激动和欣慰的。刻在骨子里对文化馆的眷恋,见到与之相关的事物,都会感到无比的亲切。而父亲将杂志交给我,深层次的含义是否将他对文化馆的那份深沉的爱恋传承于我,希望我爱上读书、写作,爱上文化馆,把他未完成的梦想,替他走完?
我感觉到肩上担负的责任和重量了,但我不能退缩,只会挺胸昂头,一步步往前走。因为,不光我一个人在努力,父亲的目光也一直盯着我前行的方向……





